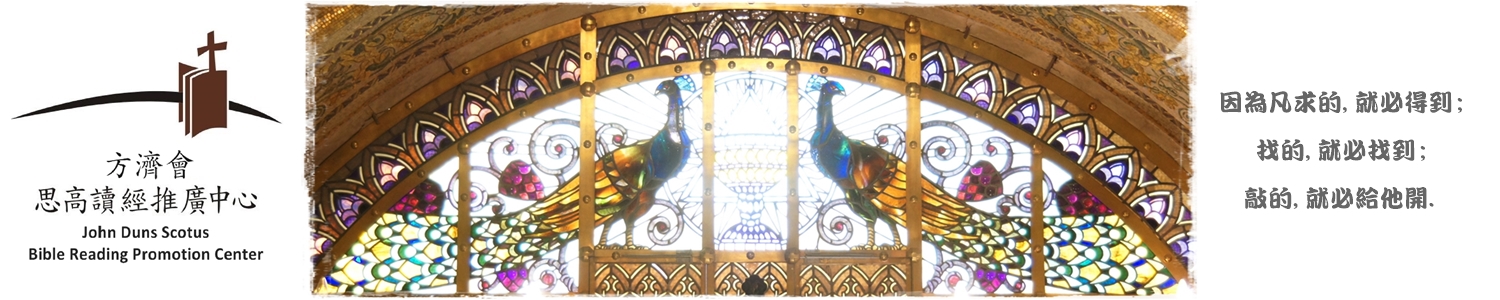18階梯
圖、文 許書寧
白冷的黎明,在祈禱聲中開始。
晨光初露,彷彿有人在濃稠的縹青顏料中注入大量清水,再緩緩攪開一般。夜色逐漸消逝,取而代之的,是越來越明亮的天光,給大地覆上一層半透明的蒼白。
我沿著修院的四方迴廊來回走動。隔著石牆,斷續傳來聖誕大殿內亞美尼亞人的祈禱聲。不禁止步,聆聽牆內渾厚的男音唱著陌生的語言和韻律。那個祈禱聲如泣如訴、痛徹心腑,宛若從深淵底端發出的哀嚎,有力、激昂、且悲傷。雖然無從明白內容,那份直接而赤裸的傾訴卻讓我全身顫慄,感覺好似被貫穿。
上主,求祢俯聽我的祈禱,細聽我的哀告!
地,張開了口,吐出生命的吶喊。
發自灰土的哀鳴穿透石牆,直達天際。
不知不覺中,眼角竟已泛著淚。亞美尼亞人的祈禱聲讓我忍不住嘆息:世界上畢竟還是有許多人,以全心、全靈、全力、全意在愛著上主,他們的天主……
一年多前,我與丈夫同遊耶路撒冷。沒有任何信仰背景的他入境隨俗,頂著小白帽進入西牆邊的祈禱所,正巧遇上某個猶太男孩的成年禮。丈夫津津有味地觀賞了全程禮儀,出來後對我說:
「雖然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,卻能夠很強烈地感受到,這群人可是『來真的』!」
八百年前,聖方濟前往聖地,因著穆斯林面對神的態度而大受感動。信仰相異者的虔誠祈禱,深深觸動了小窮人的心。在那之後,他也開始要求自己的弟兄們於固定時辰祈禱,頌揚讚美天主。
祈禱,穿越宗教、語言與文化的藩籬,直接撞擊人心。
離開白冷前,朝聖團在大殿底端的聖誕地窟舉行彌撒。
那是一場再簡單不過的祭典。礙於嚴格的時間限制與當地規矩,彌撒間沒有音樂也沒有歌曲,三十多個人摩肩擦踵,擁擠在馬槽四周,並輪流下到祭台前領受聖體。那個毫無裝飾的禮儀,將我們一舉領回兩千年前的白冷。
當時,一對年輕夫妻為了返回本城登記,從加里肋亞的納匝肋風塵僕僕地趕到,疲憊困苦,在客棧中為他們卻沒有地方。時期滿了,一個嬰孩呱呱墜地,以最赤裸貧窮的姿態來到人間。在這個沒有溫飽、沒有照明、也沒有足以枕頭之處的破舊馬廄,祂的母親將祂用襁褓裹起,放在堆置飼料的馬槽中……
是的,那是一個「什麼都沒有」的誕生場面。救世主為了愛,甘願成為「沒有」。
大阪總教區的前田万葉總主教曾經寫過一首聖誕「俳句」:
飼い葉桶 餌と成りしか 神の御子
我很喜歡這首奧蘊深藏的作品:「馬槽 願成糧草 天主子」。馬槽,是存放牲畜糧食的地方。食物提供生命,同時卻也是自身的死亡。飛禽走獸、果實穀物,無一不將自己的生命全然交托,被咀嚼、被磨碎、被消化,好成為下一個生命的延續。剛誕生的天主子,甘願在這個一無所有之處,被包裹著放入馬槽,成為永生的食糧。或許,在那小小嬰孩的誕生記號中,已經蘊含了三十多年後偉大的「死亡」。
彌撒結束後,大家陸續返回住處用早餐。我在馬槽邊稍坐片刻,與救主的搖籃道別後,隨即起身離開山洞。聖誕地窟的出入口分別為兩座石頭打造的圓弧形階梯,早被朝聖者的足跡磨得凹陷,散發出淡淡的溫潤光澤。我踩著石階往上走,不期然起了一陣暈眩,心中恍惚。
咦?
不知道怎麼回事,在那瞬間,我竟以為自己不在白冷,而是走在「另一座石階」上。那座階梯遠在耶路撒冷,同為圓弧形,也同樣被古往今來的朝聖者踏得凹陷光滑。唯一不同的是,這座階梯來自耶穌誕生的馬槽,那座階梯卻通往祂被釘十字架的加爾瓦略山。
我很是驚訝,愣在原地,久久無法動彈。
當天下午,朝聖團抵達耶路撒冷。我特別留心看了一下聖墓大殿內通往加爾瓦略的石階,發現二者其實不盡相同。無論大小、高度、顏色、材質、甚或圓弧的走向都別具一格。那樣的發現讓我滿懷感激,也因此更加確信,在白冷的觸動並非自身的記憶或經驗,而是發自聖神的感動。
生與死,原是同一件事。
白冷的耶穌,在天主降生成人的喜樂開端,同時向我啟示了十字架的苦難奧秘。
在那之後,每當我看著嬰孩耶穌的肖像,總好像看見隱藏於那柔嫩身軀之後的十字架。而當我望著十架下聖母懷抱耶穌的「聖殤」時,畫面上似乎也重疊了瑪利亞以同一姿態擁抱乳嬰的形象。
在祂身上,同時看見生與死,死與生。
這是此次我在白冷城得到的「禮物」。
後日,閱讀真福富高嘉祿神父的手記時,很驚喜地發現聖人也曾有過類似的體驗:
「1888年的聖誕節,我在白冷的聖誕地窟參加子夜彌撒,領受聖體,兩三天後才返回耶路撒冷。當我在聖誕地窟內祈禱時,感覺耶穌、瑪利亞、若瑟極為真實地臨在身旁,好似能夠直接聆聽他們的聲音。那份平安,絕非筆墨所能形容……只不過,啊,從白冷步行約莫一個小時後,聖墓大殿的圓頂、加爾瓦略、橄欖山竟已倏然眼前。無論願意與否,那條通往十字架的道路,是非走不可的了。」
(摘譯自《シャルル・ド・フーコー》聖母の騎士社)
那條通往十字架的道路,非走不可。
主耶穌說: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,除非經過我,誰也不能到父那裏去。」祂,就是道路,就是階梯。天主子自己先降到不能再低的深淵底端,為的是帶領涕泣之谷的亞當子女們重新爬上那座通往天國的梯子。
在那階梯上,天使上去下來。
天父的子女們也將經由人子的身體,下去而上來。